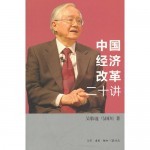盛洪:“唱红打黑”为什么错了?
在一个宪政国家,唱什么颜色的歌,以及是否打击黑社会,本来不是什么问题。但在今天的中国,“唱红打黑”就已经超出了唱歌和治安的范畴,具有某种政治技巧的味道。而这种味道却又是超出国界的。
 在一个宪政国家,唱什么颜色的歌,以及是否打击黑社会,本来不是什么问题。但在今天的中国,“唱红打黑”就已经超出了唱歌和治安的范畴,具有某种政治技巧的味道。而这种味道却又是超出国界的。
在一个宪政国家,唱什么颜色的歌,以及是否打击黑社会,本来不是什么问题。但在今天的中国,“唱红打黑”就已经超出了唱歌和治安的范畴,具有某种政治技巧的味道。而这种味道却又是超出国界的。
所谓“唱红”,就是唱某类特定的歌曲,其中的歌词具有政治倾向性,歌颂某一政治集团,经过多次反复歌唱,最后使唱歌者真的以为,这个政治集团确实有着歌词所歌颂的优秀品质和丰功伟绩。结果是,一个政治集团可以将“唱红”当作统治工具,即使自己在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歌中所唱的那样,但仍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反过来,也就会放松对自己责任的履行,甚至利用公权力侵害民众与公共利益,仍不担心会招致反对。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当中国社会承受着因毛泽东重大错误导致的大饥荒时,电台里却天天播送“东方红”歌曲,高唱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使得中国社会不但没有对毛泽东的错误加以纠正,反而走向了文化大革命。而这一运动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忠于毛泽东,是否坚持了毛泽东的错误路线。这就导致了更严重的错误。因此,“唱红”不仅会误导民众,对政治集团自己也并没有好处。
打击黑社会本来是政府的责任,但中国特定语境下的“打黑”有着如下含义,即这一行动天然合理,所以不需要受到现有法律程序以及社会惯例的约束,于是对“黑社会”的认定就有任意性,可能被用来滥用公权力,打击异已和掠夺财产。然而主张“打黑”者关心的并不是是否真正打击了黑社会,而是利用“打黑”在民众中制造一种印象,即这个政治集团在为他们铲除他们所憎恶的人,从而获得他们在政治上的拥护。更为抽象地,“打黑”可以被定义为,将人群中的一部分人定义为“坏人”(黑),然后采取非常手段打击他们,包括在肉体上消灭他们,没收他们的财产,对他们进行人格污辱和严酷刑罚,不管他们是否真有罪过,关键是让民众人心大快,在政治上拥护本政治集团。所以,“打黑”也是一种政治技巧。
“打黑”在毛泽东时代运用得最为充分,也确实得到期待的效果,有时甚至超出期待。如从打击地主开始,历经镇反,五反,反右,四清,清理阶级队伍,文革,每一次都划定一小部分人为“阶级敌人”,“动员群众”对他们进行批判和打击,既清除了异已,又赢得了民众。这成为毛泽东时代的基本治理方法。“唱红”的效果也相当“好”。由于执政党控制了所有传媒,电台和报纸充斥着对毛泽东的歌颂之词,也确实影响了民众的观念,才有文革时期,民众比赛着谁更左。
然而,从长远看,“唱红打黑”的“效用”会明显递减。当一个政治集团打击了一个被舆论和民众所憎恶的人群后,会获得一定时期的民众支持,但由于“敌人”已经被消灭,时间一长,这一支持就会下降;于是就要进行又一次的“打黑”;如此循环下去。但新一轮“打黑”的效果就会稍逊于上一轮,因而政治支持持续的时间就会变短。所以又要进行新一轮“打黑”。就这样,“打黑”运动的间隔周期会越来越短,效果会越来越差。
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即使每次被“打黑”的人数只限于人口的很小比例,但经过多轮的“打黑”,被打的人就会在人口中占越来越大的比例,到最后,就有可能不再能“发动群众”了。这就是毛泽东在二十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因而,这种政治技巧已经被运用得到了强弩之末了。在这时,青少年,即“革命小将”成了运动的主力军,以弥补“群众”在数量上的减少,和因运动频繁而导致的“斗志消沉”;而这次他要定义的“一小撮敌人”就是与他政见不和的执政党前战友。但即使是发动了“革命小将”,文化革命本身又成了前17年的浓缩版,其“打黑”的效用迅速递减。短短十年的时间里,“打黑”的周期越来越短,每一周期都更换一批“阶级敌人”,你唱罢来我登场,许多个“一小撮”就变成了“一大片”。
然而,也正是文化革命,使中国人民,包括执政党人最终醒悟了。自1949年,几乎所有的人都曾斗过别人,也都被斗过。他们终于发现,如果大家谁都不斗谁,那就是最好的情境。斗别人,就是斗自己。对于执政党的大多数成员,他们也明白了,他们当初“打黑”的规则,就是他们在文革中承受灾难的规则。只要这一规则不变,他们难免还会被打被斗。另一方面,一个执政党若要长期执政,不能再靠“打黑”“发动群众”了;因为这一技巧的效用已在几十年的运用中耗竭,所以要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而让老百姓获得物质利益,则是赢得民众拥护的稳定政策。
在另一方面,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我国虽然还有许多禁区,但在思想、文化和信息领域,总的方向是开放。各种思想,各种文化资源,各种信息纷纷涌进。再加上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互联网和微博的普及,人们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还有更大空间可以自由表达,因而当初“唱红”所能起到的作用再也不可能重现了。在今天,即使让人们唱一万遍“东方红”,也不能阻止对毛泽东错误导致的大饥荒的研究、批评和指责;甚至“唱红”本身一出现,就受到多方面的质疑。因此,“唱红打黑”只是一种对毛时代的童年记忆,它终究不能作为一个长期稳定的策略。
事实似乎证明了这一点。重庆“打黑”在开始受到了不仅重庆民众、而且全国民众的关注以致欢迎。重庆领导人也迅速从这一行动中获得了很高声誉。这说明“打黑”所利用的民众心理特征有着一般性和不变性。然而这一过程也一直遭到各界的质疑。尤其是各地派去的优秀辩护律师,将重庆公检法机构的违法行为,包括无中生有、拼凑证据,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信息记录在案,并向公众披露。最令人瞩目的是,“打黑”效用迅速递减,周期迅速缩短。在“打黑”的牺牲者被执行死刑的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打黑”的执行者因恐惧被“打黑”,逃到成都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因为他深切知道,把别人当“黑社会”打的规则也会用来对付自己。这宣告了“打黑”的破产。
在另一方面,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唱红”的政治含义。一种技巧,一旦人们发现了它的实际功用时,这种功用就不会再起作用了。反而,“唱红”成了一种令人警惕的政治符号,而不管实际上唱的什么。所以,当重庆领导人率重庆红歌队进京演出时,竟没有一个中央领导人或北京领导人出席陪同。并非他们不赞成红歌的内容,而是唯恐避之不及,沾上这一特定“红歌”的政治含义。
再从大背景来看,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再也不是毛时代的中国了。在毛时代,“打黑”不需要出动警力,那时也没有遍布全城的摄像头,只要执政党宣布谁是敌人,民众就会自动地打击他们,因为他们有着对这些“敌人”的仇恨和嫉妒;尤其是在初期,民众的“唱红”也多发自内心,因为毛不仅领导他们打倒了原来从没想过要打倒的赢者,而且还武功了得,敢于与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对抗,并且能有效约束自己的部下和军队。
而到了今天,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各种思潮并存着;对政府的行为心存更多的疑虑;更有对文化革命和前三十年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思考;知识界不会轻易被骗;还有成千上万个律师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唱红打黑”取得奇效的外部条件已不具备。在这时将“唱红打黑”作为一种政治技巧来实施,也将是一个策略上的重大失误。王立军事件说明,唱红打黑的核心人物在关键时候的举措,正说明他心中真正相信的是什么。“唱红打黑”运动所产生的表面效应如果还有一点儿欺骗作用的话,那就是欺骗了它的发起者。
更重要的是,治国要走大道,而不应用机巧。我们其实欢迎有雄才伟略的政治家。但他若想获得成功,就首先要正心诚意。他就要把天下、人民和国家放在自己及其集团之前。他就要在探究天道上下功夫。一方面,他要深知,天道要通过民意去窥得;另一方面,他也要明白,天道还要通过知识精英对历史的洞悉去领悟。这使他既欢迎宪政,又欢迎民主。走上天道,领得天命,他在技巧上拙一些并无关大局。而“唱红打黑”这样的机巧实际上违背了天道,践踏了公平正义;即使有外部条件,即使有毛的权威,像那样造成千百万人民饿死的机巧,肯可不为。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何况“唱红打黑”行诸多不义,害千万人!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