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对话:法治德治与权治
“经济观察报·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暨第二届中国改革峰会”于12月19日在北京召开。上图为年度对话:法治德治与权治。
以下为对话实录:
孟雷:各位来宾,今天我们年度对话的主题是法治、德治与权治,这不是一个普遍化的问题,它有一个共性,都是在谈的执政者的问题,因为只有执政者才有一个怎么去治理国家,采取哪种方式治理国家的选择。老百姓对国家的治理往往是间接的,不会体现在我们区隔的这么清楚的法治、德治与权治上。什么是法治?我想最近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段话是这样,一切政党,政府部门,人民等等一切的社会组织和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能有超出宪法的特权,我想这是法治的精神之一。当然,法治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所遵循的法治通过什么途径立法,来制定出来的?什么是德治呢?一直以来中国是一个在治国意识形态上比较偏向于德治的国家,以德治国,以德服人,孔夫子也说,治理国家,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必不得已而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一个行政化的管理,只是用严刑峻法来管理,人们可以会守法,但是它不会建立起价值观,那么需要什么呢?需要德治来支撑。但是,德治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它就是往往会遇到异化为主义之过,教条治国等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历史上永具公正、仁爱与智慧的帝王从来没有出现过,而且将来也必然不会有,那么德治就面临这个困境问题,单纯的德治。还有一个权治,什么是权治?我想它既不是当前的法治,也不是德治,什么是权治?我想就是以权利所欲为欲,权利可以去驱使法律,并且可以用道德,用主义,用理想为权利做包装,这就是权治。那么,法律也好,道德也好,在权治体系下都成为它的家丁,我想这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基础,待会儿我们还要就此与两位教授请教,现在有请二位上台,我们展开今天的年度对话。
今天的年度对话我们围绕法治、德治与权治展开。我们对话总要有一个定义,在什么语境下对话,我刚才做了一个简单的说明,是不是二位给我们能够有一个对这个东西更准确,更完善的一个阐述?
秦晖:我说一下,刚才你提到我们古代有所谓的靠严刑来治国,这个通常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所谓的法家。可是,我觉得靠严刑治国肯定有,是不是曾经有靠刑和法治国,即使法国可能也没有做过。关于这个,90年代有一些史学家曾经指出过这个问题,比如以往的《史书》种,司马迁讲隶有两种,一种是刑隶,一种是酷隶。而且那个时候的酷隶的确很多就是当时法律的制定者,他们对法律是非常之熟悉,也可以说,他们就是法律专家。但是,90年代的史学家指出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恰恰是这些制定法律的人,本身是非常不遵守法律的。这些人中,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其实治理国家的标准,其实并不是法律,包括他们制定的法律,就是皇帝的颜色。所谓皇帝要我整这个人,这个人即使按照他们制定的法律没有罪,也要把它弄死。如果皇上认为这个人是没罪的,即使按照他们制定的法律也是有罪的,也可以把他弄成无罪,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些人是最没有法律的。这些史学家觉得相对而言,当然那个时候是不能讲,我们现在讲的法治。但是,如果就遵守法律而言,刑隶做的远远比酷隶做的好,他们经常讲以德服人,但是真正用到法律的时候,反而是他们是严格的遵守当时的法律规定。这里面有一个代表,这个人就任的时候皇帝跟他讲过一句话,就是你要跟上级搞好关系,不能太天真了,他就有一个回答,他说律法奉公。因此,他们是遵守法律的。当然,在这个道德能起作用的范围内,他们也很遵从道德。
所以,这一段历史的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中国历史上真的存在所谓德治和法治的矛盾,无论是危害道德的,还是危害法律的,到底是谁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不仅是那个时代存在,现在其实也是同样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视道德的国家,所以这个法治好象就不必太强调。就是所谓西方的法制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中国有道德。中国所谓的有道德和所谓的法治它的确是两个东西吗?反过来中国实行法治的是中国的所谓道德吗?
贺卫方:实际上就是两个具体的侧面而已。
秦晖:有权者违法行为的时代不管道德原则还是法律原则都会被人为的践踏,我觉得无论是道德原则还是法律原则要落实到要有制约的权利。
贺卫方: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2001年或者2000年最高领导人提出以德治国,我当时感到很困惑,在这样一个缺德的社会里面,到底以什么德治国。后来中央党校的一个教授说以德治国就是三个代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被概念搞得非常困惑,比如古代的德治、法治或者古代的权治,今天我们在讲西方意义上的法治的时候,可能跟法家的法治完全不一样。我自己可能更关心是说,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间,其实也面临着人类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比如如何限制君主的权利,如何把君主的权利纳入到一个规范的轨道之中,如何限制官员的权利,如何保障人们生活的空间不被一些非法的权利,非法的力量破坏,能够获得应有的一种救济?这样的一种需求,我相信不分任何文明都是有的。那么,我们看孟子的著作里会发现,它为了限制君主的权利,处心积虑讲了很多学说,但是都没有改变这样的一种中国两千年的历史,我们一直是生活在一个威风八面的中央政府,即使这个中央政府在地方的统治存在严重的缺陷,这样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最后是社会周期性的陷入到一种,通过造反来改变权利的循环。这样的一种传统,甚至可能也影响到朱学勤教授刚才提到的后面的警察叔叔的眼神。
在我看来,我们要分析比如为什么德治永远成为一个标榜的符号?我觉得可能跟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没有一个独立的道德权威有关系。不得不把一种对社会的治理想象成为行政的权利的过程,或者司法权利的过程,同时也是行使道德教化权利的过程,这也是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国存在的一个原因。另外我们是怎样来制定出来法律规范的呢,我们会发现其实涉及到人民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些领域,比如土地纠纷,我们居然在古代是没有什么立法的,清代的时候有一些利益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从官方制定的律典来说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这样的一个立法过程,在今天看来忽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尊严及其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的财产权利,这块是在中国2000年的古典法律里面是不存在的。
如果当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对我们的权利,我们的自由提供良好的体制化的保障的时候,人民就会产生自己的需求,比如需求清官等。这是一个周期性的心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再思考包括未来十年的法治建设,我们需要检讨一下我们的法律体系如何形成,通过民主的参与使得我们某种道德的价值观念在立法中间体现,同时建立一个独立的、高素质的司法体系,保证立法在哪个过程都能得到良好的实现,给人民建立良好的预期,保障交易的安全,财产的安全,保障我们生活的自由,这可能是我们今天需要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
孟雷:我个人感觉在这个国家治理当中,法治与德治,刚才在思考,有没有这种可以在某一个平台上同时达到?我想可能就是所谓宪政,可能是法治与德治一个共同的平台。因为我们知道立宪、立法既是一个法条的建立过程,同时也是根据什么样的价值观构建法律体系的过程,我想价值观就是德治的部分,二位同意不同意?
秦晖:我觉得法律本身就包括道德判断。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这两者之间,如果用西方的法律语言讲,它也是强调成文法服从自然法,所谓自然法就是限定的,就是高于成文法律的那种人类的基本正义,我的理解大概就是这样。
孟雷:贺老师刚出的那本书,开始的时候中间打了一个“/”说以正义之名?我说这个正义合适不合适?后来觉得还是合适的。
秦晖:刚才贺卫方提到所谓的清官问题,这个清官在我们国家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类型,一种就是以道德判断为准,一个典型就是海瑞,把皇帝骂的非常厉害,但是海瑞虽然受到表彰,但是这样的清官在历史上不可能存在,海瑞原来是巡府,权利很大,后来被提拔成南京吏部尚书,南京吏部尚书不过是一个干休所所长而已。但是,我们现在也表彰清官,所谓的清官清就体现在他不怎么谈自己,而全心全意的满足皇帝的意志,在满足皇帝的意志方面他是绝不手软,敢于得罪地头蛇,可以说为所欲为。像这样的清官,我觉得是我们这个体制下真正提倡的一种清官。当然,如果贪官与这种清官相比他不喜欢,但是即使是贪官,也比海瑞那样的清官好,雍正自己讲说,最可恶的比贪官污吏还要坏的就是所谓的道不从君。这样的清官做的最可怕的一件事儿就是田文镜,他个人的确不是一个道德上贪婪的人,但是他为了满足皇帝的意志可以做任何事儿。雍正很喜欢他,就下了一个诏书说田文镜同志还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只不过受到下面的欺瞒。其实我们看到大量的都是这样的人受到表彰,海瑞那样的人,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几乎不存在,就是它能够活下来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儿。但是,像田文镜这样的清官就很多,我们且不说它是不是真正的清官,但是就算这个人是清官,到底遵从的是法治还是德治?我觉得像田文镜那种做法,就是所谓的上意所指为谕。
孟雷:我们当代也有。
秦晖: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后来大家知道《雍正王朝》之所以热播,是因为雍正是清朝的第三代领袖,到换代的时候,央视的黄金(1668.30,-2.40,-0.14%)频道又开始播了一部反映第四代领袖的戏,叫做《天下粮仓》,那是讲乾隆的。这个《天下粮仓》非常有意思,第一号反面教材就是强烈谴责田文镜草菅人命的大跃进式的做法。实际上这种做法虽然一直受表彰,田文镜直到现在还是我们历史学家非常歌颂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不要说法治,就是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新一代的君主为了收揽民心,他都要进行一些谴责的。
贺卫方:我想通过宪政来达成某种程度的法治或者德治的一种结合,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可能需要稍微想一想,比如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把自然法理解为一种道德,当然自然法有相关的道德成分,另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未来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前面几位周其仁先生,陈志武[微博]先生,包括吴敬琏先生都提到说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其实不是特别清楚。那么,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看来还要摸一段时间,其实我们未来走到哪一个地方,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我们在宪法方面也没有办法树立这样一个目标,而宪法需要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否则宪法的规范就会显得非常混乱,一部宪法内部就会非常矛盾。可以观察我们的《宪法》条文本身内部存在非常矛盾的东西,这是我需要强调的德治到底是什么。
另外,《宪法》有非常重要的条款,就是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我们今天是不是要考虑非常明确的一个规范,就是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个对于这个国家道德的拯救来说,我认为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我觉得在立法的过程中间,可能需要有一种民主的参与过程,如果整个的立法过程完全是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这样的一个思路,人们不能够参与制定宪法,涉及到一个立宪方面的根本问题,而正是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差异,才使得这个国家的道德观念融合到现代法律条文当中。但是,我们政府必须在道德问题上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性。但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法官背离法律达成某种道德要求,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秦晖:其实正义是善的基础,所以,我到觉得在今天这个不受制约的权利,它既颠覆很多基本的道德原则,也完全不受法律制约的情况下,我觉得凸显这两者的差异可以跟贺卫方讨教一下。比如前几年,你跟另外一位教授在经观上有一场争论,你们都是主张法治,但是主张法治的侧重点好象有一点不同。那么,这个事情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说不管你们两个人争的很热闹,但是我想在我们中国目前的条件下,既不可能有你所主张的那个法官制度,也不可能有他所主张的陪审团的制度。如果不把这个障碍打掉,说实在的,我觉得专业法官更重要,还是陪审团的作用更重要?我觉得这就成了一个比较悬空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两者无论哪一个能力出现对中国现在的法治状态,甚至包括对道德状态都是非常大的突破。
贺卫方:的确,比如陪审团的存在和出现是在回应着一个事实,就是司法界过分专业化,导致他们对社会常识判断能力的一种缺乏,对社会生活非常真切的东西有隔入的感觉。在英美国家陪审团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事实进行判断,陪审团只判断一个案件,是否构成了杀人、侵权,这样的事情由陪审团做,也就是事实问题,是通过证据加以证明,而不是通过法律。在这个法律解释的过程中间,经常有某种现实社会道德进步的一种因素,在这个过程中间能够通过一个严格的法律限制的条件引入在司法的判决之中。我还有一个疑问,如果像你刚才讲的,大的框架制约着两者的因素其实如果不打掉,这两者都不大可能实现。甚至,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民主的大的政治框架,大的政治框架不是一个民主体系,但是我们在审判过程中间,把民主的因素引入进来,让人民群众进入到法院,裁判案件。
孟雷:可能现有条件下会造成更大问题。
贺卫方:会更加恶化。
秦晖:当然,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这个体制不改革,也不可能真正按照西方的原则。
贺卫方:人民是被煽动起来的人。
秦晖:但是那个群众专政和所谓的陪审团和民主也没有关系。如果真要讲法治、德治,我觉得其实在你和和平的争论中,近似于陪审团就是一种德治的设计,或者偏向德治的设计,专业法官当然就是更偏向法治的设计。但是,现在的体系中已经有把这两种都处理的不错的制度基础,而且我们看到,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两者都站不住脚,我们很可能既没有德治,也没有法治,只剩下一些不受制约的掌权者的为所欲为。
孟雷:就是先确定自由,在自由的框架下建设宪政,这是一个我们说长远的愿景。但是,目前我觉得还有一个根本问题,现实问题值得讨论,就是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基于宪政的普遍原则,还能不能建立一些基本共识?也就是我们那个大框框无法打破。
贺卫方:我觉得可以有一些基本共识,比如分权,我们不搞三权分立,我们大规模的借鉴行不行,所以我觉得分权可以达成一个共识。
贺卫方:我想分权首先是横向的分权,在政府体制方面必须要切割立法、司法行政这样的权利,上下层次的分权,我觉得这个可以达成共识。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慢慢的把司法独立化,也就是司法独立能够给社会独立的自由。法律职业者的独立性,一个最愚蠢的君主才会剥夺它的独立性,因为法律职业的独立性不仅仅是把民众这样的一个比方说,不仅仅是对政府的权利进行一个分隔,进行制约,而且也把民众的不满也能纳入到一个规范的轨道进行解决,有独立的司法,人们就有司法,对社会,对国家就有希望。我前段时间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把检察院的党组撤销。
秦晖:苏联尽管有党委书记,其实我们解放初期也是一样,苏联那个时候基本上靠专业官僚治理,而且苏联的企业里头是有党委书记,那绝不是第一把手而且更不可能有宣传。
贺卫方:包括高等教育领域,它的教学过程,教学的内容,其实跟欧洲大学差不多,非常认真的学习罗马法,非常认真的学习欧洲这套传统法律体系,不像我们现在的大学里,马克思主义。
秦晖:马克思主义的成分不是很浓,主要还是秦始皇。
孟雷:实际上中国的经济严肃的计划过吗?
贺卫方:我说第三个共识,我们能否真正的确立结社自由这样的权利,就是社会中间,比如商会、工会、农会,比如律师协会,比如大学本身的自治,通过这样的方式给社会转型期的稳定性带来一种强化,人民被组织起来,人民经常被组织起来,当然政府有的时候发号施令显得不是那么容易,总是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发表不同的声音。但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其实特别有利于吸纳民众的不满,有利于让民众的经济利益通过组织起来,自我消解矛盾和冲突。我觉得分权、司法独立和结社自由,我们未来三年能不能把这三条大大的推动一步?
孟雷:这个我觉得执政者必须得认识到,无论是权利的分散和制衡,还是公民的自组织,公民社会的发育形成,还是司法的独立实际上对执政者都是有好处的,它应该认识到,这就是宪政给它构筑的一个挡箭牌。
贺卫方:我老觉得这个事儿说了多少年,怎么都听不进去,你说会不会觉得说,真正的让你新闻自由了,官跟经济之间紧密的结合全部暴露出来的,每个报纸都变成《纽约时报》了,对未来可能有好处,但是我毕竟是首当其冲,直接面对这个问题,老子就不干,老子就不搞。
秦晖:我觉得但凡搞一点就有现实的好处,最近我们一直说新政府小清新,民意是不是多少的受到正向反馈?我想任何正向改变,都会收到正向的反馈,不改变,拒绝改变,那才是放弃自己可以有的挡箭牌直面社会矛盾。
孟雷:最近我们还在讨论一个问题,您刚刚说三个共识,我还想说一个,就是现有的宪法体系,宪政体系,是不是应该成为目前社会无论你是既得利益集团,你是权贵,还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还是执政掌权者,能不能在现有的体系下先建立一些基本共识,我们叫最小公约数,在建立宪政方面,我相信大家的利益,无论是哪一个社会阶层,哪一个集团都需要保证最大的长远利益,这个最小公约数没有,对不起,真的将来可能就没有在谈更大的共同利益,最大公约数的那个机会,我有一点这种感想。
秦晖:其实这个共识只能是底线,比如各种不同宗教能够达成的共识就是信仰自由,到底哪一种宗教可以成为共识,就很难。我觉得宪政其实就是要使阶级斗争中所有的各级都受到保护的一种设计。但是,其实各个阶层都会受到长远的好处,任何一个阶层内部都由个人组成,就个人而言当然就未必了,原因并不是它的道德水平有多高,它就是为他自己着想。
孟雷:实际上现在是发生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我和贺老师都是中共党员,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秦晖:可能我党龄比你们还长,我插队的时候就是。
孟雷:真的为党着想,做所谓的普天派反而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场合我听到县委书记讲,他们共产党的那些什么事儿,共产党似乎已经跟他没有了关系了,他都已经做了一种切割,可能不是切割,有很多共同利益。但是,他已经在某一种心理上,或者什么上,可能做了一些区隔。
秦晖:其实最明显的就是,现在我们舆论管制很厉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发现这些年的舆论控制和以前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的控制说,它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现在的控制其实控制的最严的是新闻这一块。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一些管制措施已经完全成为某些很具体的既得利益者的捍卫者,他甚至也不想捍卫什么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就是赤裸裸的捍卫某些个人,某些部门,某些很具体的群体。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管制,无论从什么理由讲都是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孟雷:贺老师12点10分必须走,我们二位简单的就今天的话题法治、德治与权治做一个小总结。
秦晖:无论是法治,德治都要从宪治权利入手,否则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原则和法律原则。
贺卫方:我想建设一个宪政体制可能离不开国民的积极的参与,推动,观念方面和意识形态的改造都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我们要认识到,往往是先逐渐的形成一种法治的社会,才会有法治的顶层设计。所以,我们应该致力于对社会的一种改造,对社会结构的改造,谢谢!
孟雷:下一步的改革,如果二位老师总结一下就是无论你走法治道路,还是走德治道路,或者两条腿一起走,首先要入手的就是先改革这个权治的现状,谢谢大家!因为时间关系,今天的年度对话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分享到:
分类: 专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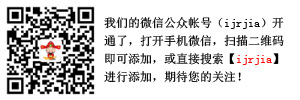


绕法治、德治与权治知识我并不是很感兴趣诶
人民没有权力,你们都是在胡扯,瞎白话!我们中国有多少即得利益单位及个人,每个即得利益者官员们都是个皇帝!人民有什么办法?被蹂躏人民又有什么办法?只有把权力还给人民,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中国才有希望!中国再出来一个将经国就好了!把权力真正还给台湾人民了,到那时就好了!中共有这样的人吗!等着吧!!!
空谈误国
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看来还要摸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