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我们向西方学习得还太不够
对我们而言,现在的问题不是西方傲慢,没有向我们学习,而是我们向西方学习得还太不够,太不深刻了。中国能够向西方学习的有科学精神,还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政治文化和集体意识中,对科学精神和民主生活的体认仍然非常肤浅,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我们对自由、人权的理解不足,需要学的东西还太多。无可讳言,中国现在法治、人权、新闻自由、理性、程序政治都存在缺陷,普通公民的尊严也难以得到保障。
 2008年12月的一天,杜维明驱车驶向美国马萨诸塞州外海的岛屿——马萨葡萄园岛。他将应约与住在那里的著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进行一场对话。
2008年12月的一天,杜维明驱车驶向美国马萨诸塞州外海的岛屿——马萨葡萄园岛。他将应约与住在那里的著名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进行一场对话。
亨廷顿被称为“上半个世纪最具影响力和独创力的政治学家”,他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和争论。由于罹患多种疾病,这位大学者早已卧床不起,而且只有白天头脑清醒。
“可是,那一天我开车迷路,迟到了几个小时,到达他的住地已经是晚上了,夫人准备了龙虾晚餐,但是教授已经休息,没有办法进行对话了。第二天清早我临走时约定,再过一个星期回来。遗憾的是,不久他就去世了”。
作为亨廷顿的多年交往的同事,杜维明先生回想起三年前的往事,备感遗憾,“我和亨廷顿有过很多接触,我们都同意,如果文明有冲突,文明对话更有必要。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广泛的沟通。”
一
2012年年初的一天,杜维明先生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研究院位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一座古典小楼里,窗外不远处就是美丽的博雅塔。
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有两大挑战,一个来自伊斯兰,另一个来自儒家文化圈。如果说,捍卫西方文明的亨廷顿是以“文明冲突论”蜚声世界的话,那么作为当代儒学思想代表的杜维明则以“文明对话”者的姿态活跃于世界的学术讲坛上。今年72岁的他是一位恂恂儒者,平易谦和。在杜维明看来,各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应该有更多的沟通、交流,形成一种全球性的“对话的文明”,“文明之间的对话历来是人类文明创造和谐的必要条件,是将来全球各地发展和平文化的重要机制。”
20多年来,杜维明一直致力于“文明对话”,对话的对象是当今(特别是西方)世界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其中既有亨廷顿这样的政治学家,也包括贝尔(Daniel Bell)、柏格(Peter Berger)、桑德 (Michael Sandeal)等社会思想家。
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学文明至今仍然具有作为全球轴心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力量,具有现代价值。在当代世界的文明对话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应该是十分积极的参与者。
二
“现在回想起来也有点奇怪,我对儒家产生兴趣是我在14岁的时候,”杜维明先生笑着回忆说。当时杜维明正在台湾的建国中学读书。其中一位老师(周文)讲民族精神的政治课,学生们都不愿意听,有时还会搞些恶作剧。可是有一天,这位老师选了五个学生,要他们来他家里,“我想教你们一点你们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对升学考试是没有用的,我教你们是完全免费的,可是有一个条件,你们不能缺课。”
杜维明和其他四位同学来到老师家里,老师第一次讲《古诗十九首》,第二次讲《大学》。“我突然感觉到,这才是我要学习的。”杜维明说,“此后,每个星期天下午1点来,5点多走,我们五个同学跟着他学习了两年。”
1957年,17岁的杜维明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台湾东海大学。第二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位海外新儒学重镇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篇宣言在当时虽然没有人理会,后来却被视为新儒家崛起的标志。当时,杜维明正在跟随徐复观先生攻读儒学。此前,他已经认识了唐君毅、徐复观等儒学大家,还曾在暑假期间旁听牟宗三讲授“中国哲学”课。
1961年,杜维明负笈美国。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先后任教于母校台湾的东海大学、美国的普林斯顿和柏克莱加州大学,1981年开始担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跻身美国一流人文学者之列。由于对儒学精神的现代认同与显扬做了大量艰苦而又颇具开拓性的工作,此时的杜维明已经成为海外儒学研究的一个代表人物。
早在1985年,著名的政治学者马若然(R·MacFarquha)在《经济学人》发表了文章《后起儒家的挑战》,认为苏联的挑战是军事力量,日本的挑战是经济力量,只有儒家文化的挑战是全面性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背景,是我提出‘文明对话’的深层原因。”杜维明说。与前辈儒家不同,杜维明长年生活于海外,增加了一个国际的面向,且有不同资源可以援用。1990年,杜维明借调夏威夷东西中心任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在这里他获得了劳伦斯·洛克菲勒的资助,大力开展了“文化中国”及“文明对话”研究项目。从那时起,他站在儒家的立场和不同文明背景的学者们进行公平的对话,互相沟通,交流互济。
三
2010年,70岁的杜维明离开哈佛大学,出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他希望能致力于人文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继承和创新。自1978年首次来大陆,34年来杜维明已经无数次来大陆了。他目睹了30多年间大陆的巨大变化,其中有惊喜,也有困惑。
刚刚进入大陆之时,就像一股清新的溪流,杜维明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界激起涟漪。可是,在许多急于实现现代化的人们眼里,儒家未免迂阔。
“1985年我来北京大学讲儒家哲学,很多人对我讲的很有兴趣,可是他们说,你要了解在中国的现实,我们这代人不可能有任何人认同儒家。20多年过去了,现在北大、清华搞中外哲学的教授不少都认同儒家。”出乎当年人们的意料,在大陆儒学越来越成为显学,那种激烈反对传统文化的气氛也已经消弭殆尽,“但是那种情绪还有,把孔子像放在国家博物馆前,在舆论的压力下又挪进去,都反映了对儒学爱恨交织的情绪,”杜维明说,“特别是现在有些人又把儒学变成了‘原教旨主义’,这是值得警惕的。”
作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杜维明清醒地指出,尽管儒学文明对于当今人类文明建设具有启发意义,却不能单独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导,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正在呈现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明显的多元化格局。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和发展是以全球文明多元化为背景的,在当代任何一种文明体系都不可能单独在全球文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我并非仅仅把儒家当成一个学问,儒家的有些价值也是我的价值,”杜维明坦率地说,“我认为,我的学术一定和儒家将来发展的命运有关系。”
杜维明夫子自道:“我是一个美籍华人,但完全认同文化中国,热爱中国的精神和心灵,也努力学作一个世界公民,希望自己没有狭隘的排外情绪,而是以世界公民的眼光来认识全球。”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现在的文化千疮百孔,但中国的‘元气’仍然很盛,也因此造成某种无知和傲慢,不管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化,满洲帝国崩溃以来,中国一直在建设现代国家”,杜维明提醒说,“建国的任务至今尚未完成,在文化基础上建设现代国家,仍然任重道远。”
“儒学不能单独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导”
《财经》:20年前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而你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文明对话”,那么在你看来,当今世界是不是存在“文明冲突”呢?
杜维明: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决不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亨氏对文化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的,是站在一种狭隘的政治学立场上,反映了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社会一些人的一种不健康的心态。尽管“文明冲突论”产生了相当影响,并且这种思想还在发展,但今后它的影响会越来越薄弱,因为它的理据有问题。
我认为,冲突不一定存在于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在一个文明体系的内部,同样会有冲突。当今世界,很多民族都面临着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的破坏之间的冲突、物质生活的提高与精神价值的沦落之间的冲突,等等。这类文明体系内部的冲突,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说很多文明体系中都存在着这类冲突。这就决定了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可以、而且应该进行广泛的对话。
《财经》:也有些学者认为,文明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例如,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就存在着矛盾,“9·11”就是这种冲突的表现。
杜维明:我不认为“9·11”是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间的冲突,(它)应该是阿拉伯世界极少数原教旨主义集团分子对美国的恐怖攻击。但正因为这两种文明之间存在深层的误会,才使极端分子有机可乘。其实绝大多数伊斯兰教徒是崇尚和平的,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明冲突,也不能否定文明对话是全球文明发展的主要趋势。
正因存在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就更有必要进行文明对话。文明间的对话历来是人类文明创造和谐条件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全球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21世纪,各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应该有更多的沟通、交流,形成一种全球性的“对话的文明”(我和池田大作的对话就以“对话文明”为题)。而且当今世界的文明对话,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史无前例,已经超过雅斯贝尔斯所说人类文明的第一次“轴心时代”。
《财经》: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里,除了来自于伊斯兰文明的挑战,提到的另一个挑战就是来自儒家文化。
杜维明:也正因此,在当代世界的文明对话中,儒学文明应该是十分积极的参与者。儒学文明至今仍然具有作为全球轴心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力量,具有现代价值。
《财经》:可是,在大陆对于儒学文明的价值仍然有严重分歧。一方面,至今仍然有许多人怀疑儒学文明的现代价值,甚至认为儒学对于建立现代国家是一个阻碍因素;另一方面,极力倡导的儒学人们又宣称,儒学将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导,在中国思想界曾经流行的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观点就认为,儒学文明将为世界文明开一条新路。
杜维明:这两种我都不赞成。
尽管儒学文明对于当今人类文明建设具有启发意义,却不能单独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导,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正在呈现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明显的多元化格局。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和发展是以全球文明多元化为背景的,这是我们谈论传统儒学的现代意义问题时的基本前提。在当代任何一种文明体系都不可能单独在全球文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正如“欧洲中心论”已经破产、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一样,人类文明发展也并不等于“儒化”。说儒学文明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只有儒学文明才有价值,其他文明系统同样有各自的重要价值同样是全球多元文明格局的组成部分。
至于儒学对于建构现代国家的重要意义,被许多人忽视了。大概除了西欧和美国以外,真正现代化成功的地区就是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怎么能说儒学是构建现代国家的阻碍因素呢?我不否认,儒学有不好的方面,我们要做的不是把儒学全盘抛弃,而是发掘其中的精华,把儒家最好的价值发挥出来,对付儒家的封建遗毒,从而实现真正的内在文化转化。
“从东亚走向世界”
《财经》: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你也曾经称赞他的著作《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是一个天才人物写的一部天才的著作”。列文森认为,儒学传统已经被中国最杰出一批知识分子批判,将来儒学对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有影响,但是不可能通过儒学来建构一个有原创性的文明,也不可能超出中国,对东亚文明、对世界文明有所贡献。儒家思想只能是“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无所为地只在心底像古玩般地被珍爱着”。
杜维明:我提出和探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就是针对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断定儒家传统业已死亡的结论而发。
我将儒学发展分为三期:第一期发展是从先秦到汉,儒学从山东曲阜走向中原。汉以后一直到唐代,主要是佛教思想的传播,儒学的发展相对处于低潮;第二期发展是从宋代到明清,儒学从中国走向东亚。儒学对佛教思想的挑战,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回应,并从某一角度成为整个东亚社会的文明体现。
《财经》:鸦片战争以后,儒学式微,儒门冷落,在“五四”时期更是遭遇重创。
杜维明:确实,鸦片战争以后100多年里,儒学几乎被埋葬、被结构了。“五四”的时候,真正讲全盘西化的人极少,但他们是精英的精英,他们以儒家传统糟粕的糟粕和西方文明精华的精华进行对比,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能救中国。结果,儒家的阴暗面泛滥成灾,真正的基本价值被解构了。他们激烈地反传统,要砍断中国文化的根,甚至呼吁“废除汉字”。
《财经》:这种激烈反传统的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
杜维明:是这样。“五四”以来每十年一大变局,1949年以后的年轻人跟传统文化基本没什么接触,因为整个社会都是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在中国人群集中的地方,中国文化竟然受到最大的残害和糟蹋,这已经是惨痛的、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一直到今天,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财经》:可是真正的儒家文化已经丧失殆尽了。
杜维明:儒家文化虽然衰微了,但是并没有消亡,因为“儒家文化圈”除了中国,还有韩国、越南和海外华人。
我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来了解中国?中国当然是一个经济实体、一个政治实体,但是从文化上来认识非常难,因为文化要经过创造、自主。因此我提出“文化中国”,这个观念包括三个意义世界:第一,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和地区主要是由华人组成的社会;第二,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第三,包括一批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无婚姻关系的、长期关怀文化中国的外籍人士。
我的目的就是,希望三个意义世界的人们来共同塑造“文化中国”。
《财经》:你将儒学搁置于东亚乃至香港、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侨之中,最终将世界各国认同儒学观念的非华人也包含在内,这是从世界主义的情怀出发对儒学所作的发展。在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背景下,继承和发展儒学似乎并非没有可能。
杜维明:第三期儒学如何发展的问题,始终是我所关注的主题。我希望中国文化能实现其现代化与世界化,儒学第三期发展必须经过相当曲折的道路,儒学必须面临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伊斯兰文化、拉美文化、俄罗斯文化、南亚文化、非洲文化,乃至东亚文化(即工业东亚) 的挑战,把它真正的内涵在一个多元的文化背景中展示出来,并在这些文化中播种生根,然后才能以康庄的姿态回到中国,健康地发展。
儒学有无第三期发展的可能?这取决于它能否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有一个创建性的回应。即儒学吸收西方文化的菁华,最终成为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乃至核心内容之一。我对此前景相当乐观。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推动儒学从东亚走向世界。
虽然我是美国的公民,但我认同的是儒家文化。不过,我认同的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儒家文化,而是强调和东亚文化乃至于世界的对话。
《财经》:从东亚走向世界,也意味着儒学的创新。
杜维明:当然,我们现在谈21世纪的儒家,它最强势的力量就在于它是有涵盖性和整合性的人文精神。和凡俗的启蒙来的人文精神相比,它的力度更大,涵盖面更全。因为它是对于个人修身的问题,人和社会的问题,人类和自然问题,人心和天道的问题。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家考虑的主要问题,一个是自由和平等,一个是效率和社会整合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大概所有伟大的宗教,都要面对生态环保的挑战,从而经过一个彻底的转化。
“不能忘记儒家的阴暗面”
《财经》:我十分敬佩你发展儒学第三期的气魄。可是,儒学到底有何现代价值,尤其是面对当下处于转型中的中国,儒学的价值怎么发挥作用呢?
杜维明:儒家的核心价值,现在的理解是“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与西方的那些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是可以进行对话的,不仅可以对话,还可以互补。
有一些价值,经过两千年的锤炼,它还是有价值。一方面必须要向西方学习,另外一方面又必须能够维持中国的特色和认同。我认为,像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权,这些价值是扎根在现代西方文明中的普世价值,而仁义礼智信是扎根在儒家文化传统,也就是东亚文明中的普世价值,它不是地方价值,也不只是亚洲价值。现在的对话为什么可能,因为人类现在遇到了新的大问题,这些不是启蒙思想家能够想象的,不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能够想象的。
《财经》:也有人说,儒家没什么了不起,它不过就是教人修身,政治建构不行,制度发展也不行。
杜维明:这是对儒家的误解。儒家传统包括三方面,一方面是核心价值,不光是修身,还包括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包含一套最核心的理论。这个核心理论是什么,它代表着的人文精神,和基督教、犹太教、道家、佛教、伊斯兰教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能不能对话,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研究。第二,儒家有非常深厚的学术传统,很多学人从注解经典来研究儒学。再来,儒家是实践的哲学,孟子讲仁道,仁道就是以人为本、造福百姓的为政之道,如果对人的尊严,对人的身心性命之学不照顾,这样的政治哲学是不符合儒家精神的,必须严厉地批判。
《财经》:现在国内一些学者讲政治儒学,甚至有“儒家社会主义”的主张。
杜维明:充分政治化的儒家,比法家还糟糕,法家只要行为正确就可以,儒家如果被充分政治化,对你的行为之外还有很多约束,态度好还不行,还得有信仰,最好是下意识的,这在以“红太阳”为唯一原则的革命思想里面暴露无遗。儒家有权威主义的倾向,但对每个人、特别是领导者有非常强烈的责任要求。权威有正面的含义,譬如说某位学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
在儒家发展的同时,不能忘记儒家的阴暗面。从“五四”以来,大家看到的都是儒家的弊端,别忘了现在这种弊端还在。“五四”时期说的封建遗毒、裙带关系、走后门、马虎、不负责任、贪污腐化等等,现在变本加厉。反而儒家的温良恭俭让倒没有,将来如果是纯粹政治化的儒家,大家都倒霉,这是儒家未来在大陆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对此要保持充分的清醒。
《财经》:那么儒学是不是可以发展出有别于现代西方的民主来呢?
杜维明:有没有儒家式的民主,是不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这都是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讲中国特色常常是一个借口,像李光耀所说的西方自由民主那套不适合亚洲,就引起非常大的批评,人们指责其为权威主义找借口,所以这条路一定要比西方民主更能为人提供自由,更能创造人权的价值和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建国工作非常艰巨”
《财经》:由于受原有教育的影响,现在不少中国人视野非常狭隘,认识世界时总是带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成见和排斥,也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排斥。
杜维明:在21世纪除了文明对话以外,还有两个对话:一个是科学和宗教的对话,另外一个就是现代和传统的对话。这些方面中国做得很差。比如,中国现在最大的考验之一,就是汉文化如何与藏文化、维吾尔文化对话。不了解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也就是不了解他们的终极关怀,他们的心灵世界,和他们不惜以生命来捍卫的意义王国。我强调,对宗教我们应该有起码的认识。
《财经》:在中国现在所谓经济崛起的背后,其实有许多问题都没有解决,反而是随着经济实力的膨胀,很有可能产生更大的冲突。
杜维明: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你说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按人均计算是日本的十分之一,在世界各国中排到九十多位左右,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有些人宣扬什么“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意思就是说其他国家,比如印度和非洲都来学习。可是,中国发展经济的模式能学习吗,中国的政治模式能学习吗?有学者说,中国可以走和欧美自由民主政治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另外一条路。这是一条什么路?
对我们而言,现在的问题不是西方傲慢,没有向我们学习,而是我们向西方学习得还太不够,太不深刻了。中国能够向西方学习的有科学精神,还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政治文化和集体意识中,对科学精神和民主生活的体认仍然非常肤浅,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我们对自由、人权的理解不足,需要学的东西还太多。无可讳言,中国现在法治、人权、新闻自由、理性、程序政治都存在缺陷,普通公民的尊严也难以得到保障。
《财经》: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不需要民主,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
杜维明:最近的台湾选举非常成功,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候选人的素质,已达到了超越欧美的最高水平(马英九是哈佛法学院的博士,蔡英文是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
从投票率来看,更是值得注意。 美国一般选举的投票率能到达40%就很难,台湾这次竟高达80%以上。这次选举真正值得恭贺的是台湾的选民,这是因为台湾民主政治经验的底蕴厚。这也正证明了中国文化基础并不排斥民主等现代文明。我讲过好多次,儒家的人格的发展最适合的环境就是自由民主社会,因为在一个传统的专制社会和现代的权威社会里,不能充分发挥人的道德潜能。
坦率地说,现在的中国是一个没有文化支撑的社会,向市场社会滑坡的危险极大。不只政府,媒体、企业、学术界,就连宗教界也不例外。中国还没有走出自己的模式,还在摸索,如果按照中医的说法,中国现在的“气”很不顺。中国精神世界千疮百孔,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元气”还很充沛,虽然有时和欧美各国谈判时暴露出无知和傲慢。可是我坚信中国的知识精英不管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变化气质的可能性很大。
以前日本人对中国正面肯定的超出80%,经过毒饺子、毒奶粉等事件,现在已经降到30%以下。可是如果我们能把忧患意识落实在生活世界之中,逐渐达到大陆周边的水平,即可恢复数千年儒家文化孕育我们的基本的做人的道理, 国际形象即可大大的改建。
《财经》:现在中国的经济还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国力在增强,但是对于中国的前景,很多人越来越担忧。
杜维明:你讲得是对的,大家对于现在的道德沦丧、贫富不均、城乡差距、腐败蔓延等等现象忧心如焚。
任何一个民族,假如它是有动力、有远见的,它就会通过对自己文化的反思,深刻理解文化中的最高理想。理想本身是一个境界,是一个视野。例如,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就是有理想的,譬如人人生而平等,虽然理想从来没有完全落实。否则20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就不会有丰厚的象征资源。
《财经》:今天的中国社会缺乏理想。
杜维明:今天中国社会有理想吗?没有,现在大家在谈传统文化里的“天下”,都是零零碎碎的,没有一整套人文精神。但“天下”的理念即是难能可贵的象征资源,美国目前的政治文化中就没有这种全球性的视野。
仅仅发展经济是不够的。经济之外,还要发展文化。中国有渊源悠长的文化,要在文化基础上建设真正的现代国家。如果说西方国家是先有国家、后有文化。而中国已经有5000多年的文化了,满族帝国崩溃以来,中国一直在建设现代国家,到现在100年了,至今还没有完全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国、大多数成员都引以自豪的文明大国。
中国的建国工作非常艰巨,在建国的过程中将碰到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文化的资源是非常丰厚的。中国要正面对待自己的问题,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实现真正的内在的文化转化。把儒家最好的价值发挥出来,竭力消除儒家的封建遗毒。因为儒学传统不仅是中国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也是一种全球文明健康发展的丰富资源。
《财经》记者 马国川
分享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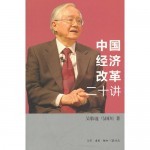
重提“德先生”和“塞先生”,说明了这两个问题没解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