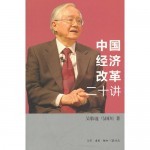薛兆丰:若有用,就能活
英文有句话,叫“If it pays,it stays.(若有用,就能活)”。意思是:越是对人类有用的动物,人类玩得越多、杀得越多、吃得越多、用得越多,也就饲养得越多。这种动物更干净、更健康、更肥壮,不容易灭绝。
 归真堂从活熊身上提取胆汁制成药品销售,已有20多年历史。该企业最近申请上市,动物保护主义者激烈反对。大批媒体记者蜂拥到工场,舆论关注的焦点是究竟“熊疼不疼”、“熊有无自由意志”、“熊是否生活在其最自然的状态之中”等问题。我认为舆论看偏了:重点并不在“熊疼不疼”,而在于究竟是某些人“心疼”重要,还是另外一些人的“病疼”重要。换言之,这不是人熊之争,而是人人之争。
归真堂从活熊身上提取胆汁制成药品销售,已有20多年历史。该企业最近申请上市,动物保护主义者激烈反对。大批媒体记者蜂拥到工场,舆论关注的焦点是究竟“熊疼不疼”、“熊有无自由意志”、“熊是否生活在其最自然的状态之中”等问题。我认为舆论看偏了:重点并不在“熊疼不疼”,而在于究竟是某些人“心疼”重要,还是另外一些人的“病疼”重要。换言之,这不是人熊之争,而是人人之争。
毫无疑问,熊当然有点疼,其自由意志当然受到了侵犯和扭曲,它们当然还未能生活在最自然的状态之中。这是不容争辩的。问题是,那又怎样?如果“熊疼”足以成为禁取熊胆的理由,那“鼠疼”也足以成为禁止医药实验的理由,“牛疼”也足以成为禁止挤奶的理由,“狗疼”也足以成为禁止爱狗人士阉割宠物的理由……照这样的逻辑,我们还真要问问:动物怎么就不能平等地享受人类赋予的权利?
我说过,相对于熊疼不疼,我更关心人疼不疼:小女孩们被家长送去苦练芭蕾时疼不疼?未成年人缺乏判断力,而家长往往是逼迫加利诱,让她们承受极不自然的扭曲和伤害,以博取看客的掌声。这是否道德?看客们追求的快感,又是否是必需的?历史上已有的视频片段,或改用动画制作的芭蕾舞蹈,难道还不足以满足看客的需求?
显然,上述活动都具有“引起疼痛”、“影响终身”、“强加意志”、“并非必要”等特点。如果要禁止,那就都应该禁止。可见,要具有建设性地讨论,就必须先转换视角,不再关注熊疼不疼,而是讨论谁有权决定让熊疼,谁又有权决定让人疼。
一项权利,代表一种受到社会认可和维护的、对商品的用途作出有效选择的能力。这是说,一个人的某项权利,是依靠社会其他成员的主动赞同和维护,才得以产生的。你即使具有对某商品的用途作出选择的能力,但只要你的所作所为不受社会其他成员的主动赞同和维护,那么你就不具备这项权利。土地是你的,但你未必有权盖高楼挡住邻居的视线;房屋是你的,但你无权在后院做原子能实验;水果刀是你的,但你肯定无权用来打劫,否则拥有水果刀,就了拥有整个世界。
世上没有“天赋权利”这回事,尽管人们往往爱这么说,以此来强化自己的主张或信念。世上有的只是“人赋权利”。例如,每个人似乎都拥有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但在大多数国家,社会却剥夺了每个人选择安乐死或出售器官的权利;又例如,每个人都拥有对自己电脑的产权,但如果电脑里藏有儿童色情图片——或仅仅是儿童色情漫画,那也会触犯法律。显然,个人拥有何种权利,是人与人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开天辟地就自然而然地清楚界定并一成不变的。
近年来,动物保护的意识在国内越来越普及,部分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吃饱了,开始更多地关心自己心灵上的感受。正常人都具有“同情的生理机制”:看见熊疼,就会情不自禁地设想自己如果是熊,那也会疼,于是产生了心疼的感受。为了减少自己“心疼”,便想到去限制别人本来享有的产权,或增加别人忍受“病疼”的可能。
以个人倾向而言,我认为养熊者有权取熊胆,养狗者有权阉割宠物,父母有权磨练子女;但以中立观察者的角度看,我认为动物保护主义者有“主张权”,可以呼吁社会限制他人产权,但归真堂至今仍有“产销权”,不仅有权饲养、摘取、生产和销售,而且有权申请上市。
如果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自己的感受要比熊胆制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选择权更重要,那就应该筹措或购买宣传资源,博取舆论的支持,通过修改法律来达到目的。中国要走法治道路,要建立法治传统,要避免让个人感受凌驾于法律程序之上,那么归真堂事件也是一块试金石。
我还是喜欢从经济的角度来推测。其实,不论熊胆爱好者和动物保护者怎么争,大部分人也还是看代价来选择立场的。棕熊命运,既不取决于它疼不疼,也不取决于它的自由意志,而只取决于熊胆的药效。如果医学能马上证明,熊胆不仅解酒护肝,还滋阴壮阳、专治艾滋,那熊胆爱好者就能得胜,棕熊就会在私人的悉心照料下,开枝散叶,代代相传;相反,如果药效微弱又无法确证,动物保护主义者就更容易占上风,棕熊就会像其他受政府保护的动物一样,从被作为“私有财产”来对待,逐渐转为被作为“公有财产”来对待。
那么,有确定主人的动物更幸福,还是无确定主人的动物更幸福?从个体的角度看,不好说;但从种群的角度看,英文有句话,叫“If it pays,it stays.(若有用,就能活)”。意思是:越是对人类有用的动物,人类玩得越多、杀得越多、吃得越多、用得越多,也就饲养得越多。这种动物更干净、更健康、更肥壮,不容易灭绝。
分享到: